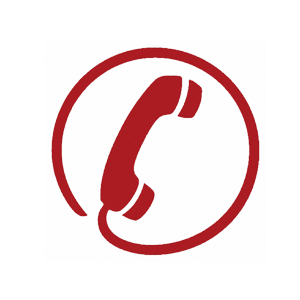刷到一个印度记者的自述,有点意思。他说来中国考察,头两天人是恍惚的,完全没有办法理解。专门跑去我们这边算“贫困艰苦”的贵州看,结果发现,这边的“贫困”和印度的“贫困”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。天壤之别。那个原本装着满满优越感的“偏见行囊”,在踏入贵州大山的第一刻起,就被现实撕了个粉碎。这就好...
刷到一个印度记者的自述,有点意思。他说来中国考察,头两天人是恍惚的,完全没办法理解。专门跑去我们这边算“贫困艰苦”的贵州看,结果发现,这边的“贫困”和印度的“贫困”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。天壤之别。
那个原本装着满满优越感的“偏见行囊”,在踏入贵州大山的第一刻起,就被现实撕了个粉碎。
这就好比你是抱着去看“原始部落”的心态出发,结果一脚迈进了一座“科幻之城”。这位原本蓄意要在中国的“穷山僻壤”里挑刺找心理平衡的印度记者,估计做梦也没想到,这一趟考察竟成了他职业生涯里最彻底的一次“认知崩塌”。
他没有像预想中那样,用镜头捕捉到落后与绝望,反而上了一堂名为“什么是现代化国家意志”的震撼课程。
如果你问这位记者,什么叫“绝望”,他出发前一定会告诉你,是中国西部那无法逾越的天堑。他特意避开了自带滤镜的北上广深,一头扎进贵州,满心以为等着他的是摇摇欲坠的盘山泥路。然而,现实给他的第一个耳光就是那个立在云端的“基建狂魔”。
你能想象吗?在原本应该这辈子都与世隔绝的峡谷深处,厚重巨大的桥墩像定海神针一样扎根,高架桥并不是贴地而行,而是霸道地直接架在云雾里。
当他坐在高铁上,窗外是一闪而过的悬崖和云海,车身却稳得连水杯都不晃,这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让他整个人都是恍惚的。
在印度,这种工程难度基本等同于天方夜谭,属于写在纸上都嫌吹牛的程度。但在这里,车在天上跑,人在画中游,竟然成了最稀松平常的日常。
他原本笃定这些都是撑门面的“形象工程”,是演给他看的戏,于是他决定往更深处钻,去那些地图上都未必标得清楚的小村落,誓要揪出那些被遗忘的“烂泥塘”。
如果说云端的大桥只是让他感到视觉震撼,那么深入村庄后的细节,则是彻底摧毁了他对“贫困”二字的定义。
按照他的逻辑,真正的贫民窟应该是浑浊的坑水、满地的泥泞和苟延残喘的生计。可当他真正把脚踏在深山的土地上,脚下踩的是硬化水泥路,一直通到村民的家门口。
随手拧开一家农户的水龙头,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——要知道,在印度的许多富裕街区,全天候清洁水源都是奢侈品。
更让他感到“荒谬”的是空气中看不见的信号。在这种被大山重重包裹的地方,电子设备屏幕上的5G信号格居然比国际大都市还要满、还要稳。
眼前那些皮肤黝黑、看似只有传统农耕经验的老人,从口袋里熟练地掏出智能手机,刷着视频、和远方的儿女连线,甚至扫码支付买卖农货,那动作的熟练度比他老家很多人都高。
冰箱、洗衣机、彩电,这些代表现代生活的电器塞满了原本他不屑一顾的农房。他不得不承认,自己那个用来衡量贫富的坐标系,在这里彻底失效了。
在他原本的设想剧本里,贫困山区的教育必然是漏雨的教室和眼神黯淡的孩子,就像印度贫民窟里那样,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都是奢望。
但他看到的景象,简直是在狠狠刺痛他的神经: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,色彩鲜艳的塑胶田径运动跑道在阳光下反光,孩子们的午餐不仅热乎,而且营养搭配均衡。
这种对比是最残酷的。因为这不单单是吃饱饭的问题,这背后意味着中国在这个哪怕最偏远的角落,也在不计成本地为下一代铺平阶层跃升的道路。
中国扶贫的逻辑,从来不是简单的施舍食物,而是通过教育把这些人从大山的禁锢中拽出来,塞进现代文明的发展快车道。这种对未来的投资力度,让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敬畏,甚至是一丝恐惧。
这位记者最终没有发回一篇“找优越感”的报道,反而写下了一份充满挫败感与清醒的观察录。
他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:把基站修到人迹罕至的山顶,把大桥架在几乎没办法施工的云端,如果单从商业回报率算账,全是彻头彻尾的“亏本买卖”。世界上没几个资本家愿意做这种事,也没几个政府有能力做这种事。
但这恰恰是中国最可怕的地方。为了区域平衡,为了不落下一个人,国家意志可以凌驾于商业逻辑之上,强行抹平地理上的鸿沟。
这种通盘布局的决心、令行禁止的执行力,以及举国之力倾斜资源的调动能力,让印度的治理模式相形见绌。
所谓的“贫困”,在中印两国根本不是同一个维度的话题。印度的贫困还在解决“生存”问题——如何让人活下去;而中国所谓的贫穷的地方,讨论的是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,是如何享受同等的现代化服务。
他在离开时坦言,哪怕把全套的设计图纸和施工队搬过去,印度也抄不了这份作业。且不说资金和技术的缺口,光是这份誓要“天堑变通途”的决心和执行效能,印度就在五十年内难以望其项背。
本来想来看个笑话,最后却发现小丑竟是带着有色眼镜的自己。他没看到预想中的苟延残喘,只看到了一个庞大国家崛起时那股不可阻挡的雄浑气势。
信息来源:《印媒记者惊叹中国贵州发展:这里的贫困与印度不在一个维度》环球网
 中文(简体)
中文(简体)